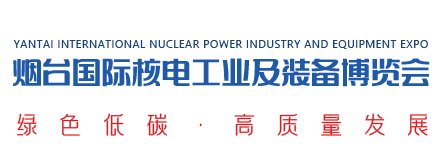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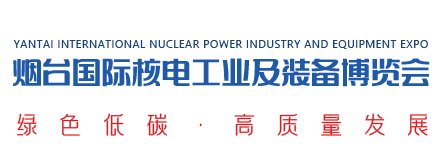

中国核电建设进程加快。
去年8月国家获批5个核电项目(11台机组)后,近期,又核准浙江三门三期、广西防城港三期等5个核电项目(10台机组),总投资超过2000亿。
与此同时,国家能源局出台文件,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参股核电项目,释放市场化信号。
图:我国大陆各省份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情况(截至2024年)
在沿海核电快速布局的同时,内陆核电何时破冰话题再度引发热议。
尽管国家能源局尚未明确时间表,但现实需求已倒逼政策转向。
火电受碳达峰、碳中和约束,占比逐年下降。西南地区水电易受季节和极端天气影响,且电力外送任务逐步加压,电力缺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。
2024年和2025年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》蓝皮书连续建议,“针对华中等电力缺口突出区域,尽快启动核电项目”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更是提出“2030年前后启动中部地区核电项目”的时间框架。
内陆核电站破局看似水到渠成,实则暗礁密布。
福岛核事故的集体记忆仍在刺痛公众神经,长江流域人口密集区的生态隐患成为最大阻力,且内陆核电站在冷却水、应急疏散等方面要求更高,还有待进一步验证。
内陆核电站的前世今生
中国的核电全部位于沿海、没有内陆核电的做法,并不是全球核电的主流。
全球内陆在运、在建核电机组比例高达64%和44%。
全球核电装机数最高的美国,98台核电机组有84台分布在内陆,其中密西西比河流域有32台核电机组。排名第二的法国,58台核电机组中有40台位于内陆。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已得到充分验证。
事实上,内陆核电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鲜事物。早在1977年,湖南小墨山核电站就已进入规划,这也是中国内陆规划最早的核电站厂址。
而中国为巴基斯坦设计建造的恰奇玛核电站也位于内陆地区,投产至今安全业绩良好。
2003年后,内陆省份频发“用电荒”,且核电首次纳入国家电力规划,四川、重庆、江西、湖北等省市提出核电项目计划,掀起一轮内陆核电项目规划热潮。
2003年四川成立省核电筹建领导小组,负责协调核电筹建工作,开展四川核电前期工作,最终确定南充市蓬安县三坝乡作为核电站的首选厂址。按照规划,三坝核电站的最终装机容量为400万千瓦。
此外,四川还在宜宾、泸州和南充找到了三个适宜修建核电站的厂址。
四川期望强化核电在能源格局中的作用,构建“水电为主、核电为补”的供应体系,改变单一依赖水电的现状,提升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安全性。
四川这一构想多年后得到反向印证。2022年夏季,四川遭遇极端高温干旱,水电发电量锐减,全省供电能力大幅下降,暴露过于依赖水电的脆弱性。
几乎就在同时,重庆也启动了核电项目的前期工作,并联合中电投向国家发改委递交了项目申请书,初步选址涪陵白涛镇的816核工厂,后来改在南沱镇石佛村,目标直指建设国内第一座第四代核电站。
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为85亿千瓦时,可部分缓解重庆的缺电压力。计划2013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。
随后,重庆还在丰都、石柱和忠县推进核电项目的选址。
不过,川渝规划的核电项目受制于地质风险、长江上游水源污染风险及生态敏感性争议等问题,推进缓慢,并没有突破审批瓶颈,未来需在安全论证与公众沟通中寻找突破口。
而华中地区的湖南桃花江、湖北咸宁、江西彭泽等核电项目,因起步早、前期投入多、技术条件成熟且地质安全,再加上该地区能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,于2008年前后便相继获批,推进速度更快。
这当中,曾被冠以“内陆第一核电站”的湖南桃花江项目,计划在2011年正式开工,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,总装机容量为500万千瓦,总投资670亿元。
2011年3月的“黑天鹅”事件——日本福岛核事故,全球聚焦核电安全问题。中国随之暂停新核电项目审批,已获批的内陆核电项目也全部停工,陷入停滞状态。
截至2011年底,湖北咸宁核电累计完成投资约34亿元,湖南桃花江核电前期投入达38亿元;江西彭泽核电截至2019年底,累计投资约38.96亿元,这些项目均被迫搁置。
华中地区获批的三大核电项目命运尚且如此,川渝核电项目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了。2016年南充发改委安抚当地网友称,在国家暂停情况下,不可能推进三坝核电站项目。而重庆核电项目规划已不再出现于公开文件中。
2012年10月,相关部门在全球最高安全标准的前提下,有限度恢复了核电项目建设。2019年,中国核电闸门重启,此后获得核准的核电机组逐年递增。
但内陆核电在中国始终未能破局。
时至今日,内陆核电仍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,一旦涉及到内陆核电议题,民众是谈核色变。
因为如果一旦发生了大规模核泄漏,在最极端的情况下,沿海核电的核污水可以向大海里排放,事故后果相对可控。
而内陆核电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,这必然对公众的生活生产及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。
内陆省份争取核电重启的考量
尽管核电项目推进严重受阻,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内陆省份却并未放弃相关规划。
2013年至2016年,湖南代表团曾连续四年向全国两会提交“重启内陆核电”建议。
湖南方面认为,桃花江核电项目各项准备工作均领先于其他内陆核电项目,完全具备开工建设条件。
2022年5月,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能源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,按照国家规划安排做好核电厂址保护工作。
2024年11月,湖北省咸宁市在《发展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方案》中表示,“做好核电厂址保护,全力争取内陆核电突破。”
内陆省份积极争取核电重启,表面是为缓解能源短缺,提高电力保障能力,减少碳排放,更深层目标是通过产业链延伸、技术溢出效应撬动区域经济转型。这一战略与国家“双碳”目标、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契合。
事实上,美国沿密西西比河、法国沿罗纳河布局的核电站,均凭借“核电+流域经济”模式,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。
以江西彭泽核电站为例,前期投入已超38亿元,带动过当地建材、运输等产业短暂繁荣,停工后相关服务业陷入萧条。复工后,此类产业将重新激活,并衍生出专业化运维服务市场。项目建成后,预计年税收达20亿元,远超传统产业贡献。
四川作为中国核工业重镇,产业基础雄厚:拥有压水堆核电燃料组件生产基地,全国超60%的核电产品、50%以上大型电站铸锻件在此产出,“华龙一号”中的“四川造”核电装备已实现出口。
值得关注的是,成都瀚海聚能探索的核聚变路线,有望攻克内陆核电在水资源制约、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核心难题,为内陆核电发展开辟新路径。
若核电项目成功落地,四川将以此为契机,加速核电装备制造集群的培育壮大,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,并依托“华龙一号”出口巴基斯坦、阿根廷等国际市场的经验,进一步拓展核电装备海外贸易版图,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。
同时,凭借深厚的核电产业基础,四川还可推动瀚海聚能的核聚变技术走向工程实践,加速其商业化进程,由此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动能。
关键节点曝光,内陆核电重启不容置疑?
内陆核电站重启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。
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推测,为实现碳中和,到2060年中国核电应有4亿千瓦投入运行、发电量占比将达到20%左右。
而按照目前的选址条件和规范,在沿海地区的厂址建设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,极限总规模约为2亿千瓦,只占完成碳中和目标必需的核电装机容量的一半,其余部分只能布局在内陆地区。
有预测显示,到2035年左右,中国核电发展规模将达约2亿千瓦,这一规模与沿海核电备选厂址的极限总容量相当。据此推测,内陆核电建设有望被提上议事日程。这一预测与力挺内陆核电发展的舒印彪所提出的“2030年前后”时间节点相契合。
除此之外,第四代核电有望成为内陆核电放开的重要契机。
我们知道,常规核电站(如压水堆、沸水堆)需要大量冷却水进行堆芯冷却和热力循环,因此选址多集中在沿海或大型河流沿岸。内陆地区水资源相对匮乏,且淡水生态敏感,导致公众接受困难,内陆核电站落地受阻。
而第四代核电通过冷却方式的革新,彻底改变了传统核电对水资源的依赖模式,为内陆布局核电提供了颠覆性解决方案。
如钍基熔盐堆,无需外部水源冷却,只需少量水用于辅助系统,甚至可通过干式冷却技术实现“零水耗”运行。
同时,第四代核电通过被动安全系统和自动停堆机制,在极端事故或自然灾害下仍能保持安全状态,彻底改变了传统核电对主动干预的依赖,将提升社会信任并降低了政策阻力。
2023年12月,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——山东石岛湾核电站实现商业运营,被誉为“不会熔毁的核反应堆”,为未来中国内陆地区安全发展核电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The Website Supports All Mobile Terminal Design Support:©Bootstrap